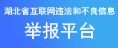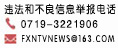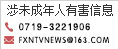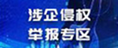房县新闻网讯 我童年的村庄张湾,东接红莲村,西靠龙驹山,北依鱼尾河,静静地卧在山坳深处,宛如一朵含苞的睡莲。村里的老人们总爱指着起伏的山势说:“你们细看,这山形多像一朵初开的莲花——红莲村是那绽放的花瓣,龙驹山是托起的莲叶,鱼尾河是摇曳的茎蔓,而咱们张湾小学,就端端正正地落在花蕊中央。”这个诗意的想象,如同一粒永不融化的冰糖,不仅甜透了我的整个童年,更在往后的岁月里,成为我心中最温柔的乡愁。

记忆里的校舍,是全村人用最质朴的匠心建造的。我至今还记得,父亲和叔伯们光着膀子,喊着号子,一夯一夯地将黄土筑成墙壁。新垒的土墙糙得像砂纸,我们这些小淘气追逐打闹时,常常被墙皮划破手指。屋顶架着从后山砍来的松木,歪歪扭扭地承托着青瓦;最难忘的是那块黑板——三块旧门板拼接而成,刷了厚厚的黑漆,边角的木刺时常扎着老师的手。可就是在这简陋的教室里,李老师那清朗的声音,将“人之初,性本善”的启蒙,将“ABC”的新知,一字一句地刻进我们心里。
窗棂上绷着的油纸,是我们童年的琴弦。每当山风掠过,便奏出“呼嗒呼嗒”的乐章;雨天时,雨点敲击油纸的声响,伴着我们朗朗的读书声,汇成一曲独特的山村交响。晚自习时分,二十余盏煤油灯在课桌上摇曳生姿,火苗随着我们诵读的节奏轻轻舞动。家境好些的同学点煤油灯,那蓝汪汪的火苗沉稳安静;我们这些孩子则点松油梗,橘红色的火舌“噼啪”作响,裹挟着松脂特有的焦香,与墨香、土香交织在一起,飘出窗外,融进大山的夜色里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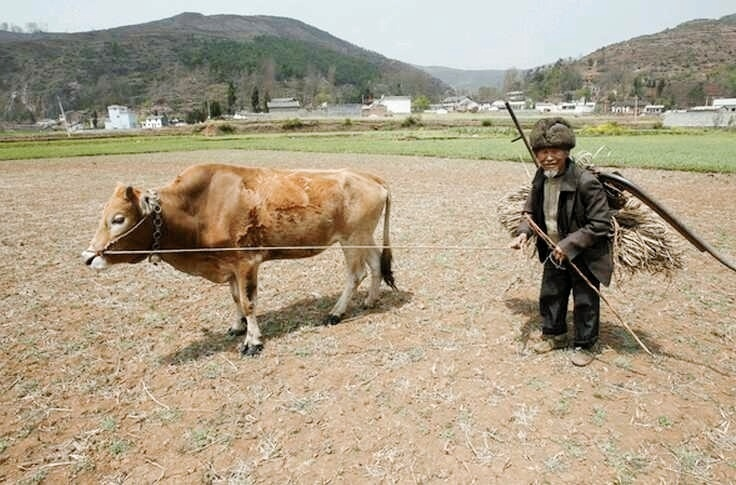
那时的操场,是我们这群野小子的天下。黄土地被无数双小赤脚踩得如陶器般瓷实,雨天不积水,天晴不起尘。我们在这里滚铁环、打陀螺、斗膝盖,个个像脱缰的小马驹。我最拿手的是滚铁环,用一根铁钩驾驭着圆环在操场上飞驰,铁环滚过地面的“哗哗”声,至今还在耳畔回响。
老柳树下,我们仰头看阳光从枝叶的缝隙间筛落,碎金般的光斑在汗津津的脸上跳跃。有时玩得兴起,索性脱了布鞋,赤脚踩在温热的土地上,那种从脚底直达心尖的暖意,成为记忆中最踏实的温度。
最难忘的,是建新学校的那些日子。
全村人勒紧裤带凑钱,每户按人口人均出八十元,在那个一分钱掰成两半花的年代,这是一笔能让腰杆弯下去的数目。可我记得清清楚楚,父亲从木箱底取出那叠皱巴巴的票子时,眼里闪烁的不是心疼,而是希望的光芒。他对着忧心忡忡的母亲说:“再穷不能穷教育,再苦不能苦孩子。咱们这辈子就这样了,可不能让孩子走咱们的老路。”
那个暑假,我们这些半大孩子也成了建设大军中的一员。天刚破晓,我就跟着哥哥们抬着小竹筐去运砖瓦,山路坑洼,背上的砂石越来越沉,汗水在脊梁上汇成小溪,把粗布褂子浸得能拧出水来。可每当看见新校舍的墙又高了一截,心里的欢喜就像春雨后的竹笋,一个劲儿地往上冒。

新校舍落成那天,全村像过年一样欢腾。雪白的墙壁晃得人睁不开眼,明晃晃的玻璃窗能照见人影,最神奇的是那一按就亮的电灯——我们这群孩子反复按着开关,看教室在明暗之间转换,仿佛在施展什么魔法。坐在光滑的木桌前,抚摸着墨绿色的新黑板,我忽然懂得了什么是希望,什么是未来。这所凝聚着全村心血的学校,不仅是我们求知的殿堂,更成了山村通往外部世界的一扇窗。
那些年的校园,处处涌动着蓬勃的生机。特别记得有一年中秋,月华如练,我们坐在操场上听陆老师、杨老师讲“嫦娥奔月”的故事。月光如水银泻地,把崭新的校舍镀成了一座银色的宫殿。杨老师指着天上的明月说:“你们要像这月光一样,将来不管走到哪里,都要记得照亮家乡的每一个角落。”那句话,像一粒饱满的莲子,在我心里深深扎根。

今年中秋,我特意回了趟张湾。
山岗还是那座山岗,莲花的轮廓在暮色中依稀可辨,只是那托着校舍的“花蕊”已然荒芜。老柳树还在,只是树皮皴裂,枝条低垂,像是在默默叹息。校舍的白墙在月光下泛着清冷的光,墙皮剥落处露出岁月的伤痕。铁门上的锁已经锈成暗红色,我用力一推,门轴发出沉重的一声“吱呀”,如同一位老人深长的叹息。
路过的老邻居认出我,摇着头说:“停学两年啦,最后一个娃娃去年也转到镇上了。老师们都调走了,教室都空着哩。”望着空寂的校园,我的心像被什么东西紧紧攥住。那些琅琅书声,那些欢腾景象,那些在月光下听故事的夜晚,都到哪里去了?恍惚间,我仿佛又看见那个坐在操场上的少年,正仰着脑袋,痴痴地听着老师的教诲。

然而,当我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驻足良久,一种更深沉的情感渐渐升起。这所学校的兴衰,何尝不是中国乡村变迁的缩影?从土坯房到新校舍,从煤油灯到电灯,我们这一代人亲历了教育事业的天翻地覆;而从书声琅琅到如今的寂静,又折射出城镇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阵痛。
莲花的意象忽然在我心中豁亮起来——莲花之可贵,不在于始终盛开,而在于深植淤泥的根茎。即便花叶凋零,只要根脉不断,深埋淤泥中的藕节依然积蓄着力量,等待下一个春天破冰而出,重现“接天莲叶无穷碧”的盛景。

张湾的校舍虽然静默了,但教育的种子早已随风远播。从这里走出去的孩子们,如今正在大江南北的各行各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。而这座空置的校园,这座曾经承载着梦想的“莲花台”,也正在等待着新的使命——或许它将转型为乡村振兴的培训基地,让乡亲们学会新技术;或许将成为特色产业的工坊,让山里的珍馐走出深闺;或许会以其他形式,继续滋养这片深情的土地。
月光将我的影子投在斑驳的墙上,与儿时的记忆重叠。我忽然明白,变迁是时代的必然,而守望是我们的选择。正如那朵莲花,花开花谢是自然规律,但深埋泥土的根茎永远保持着绽放的渴望。作为从这片土地走出去的孩子,我们不仅要怀念过去的芬芳,更要为明天的绽放积蓄力量。

离去的路上,晚风穿过柳枝,发出飒飒的声响。恍惚间,我仿佛又听到了当年的读书声,看到了操场上奔跑的身影,感受到了那份永不褪色的温暖。这声音穿越三十几年的时空,在我心中激起回响:教育的光芒不会熄灭,乡村的根脉终将延续。千千万万个张湾的故事,正在汇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洪流,如同莲花,在时代的池塘中次第开放,生生不息。而我们这一代人,从山岗走向世界,又从世界回望故乡,必将以赤子之心,在这片深情的土地上,续写新的绽放——让每一朵莲花都不负春光,让每一个春天都值得期待。